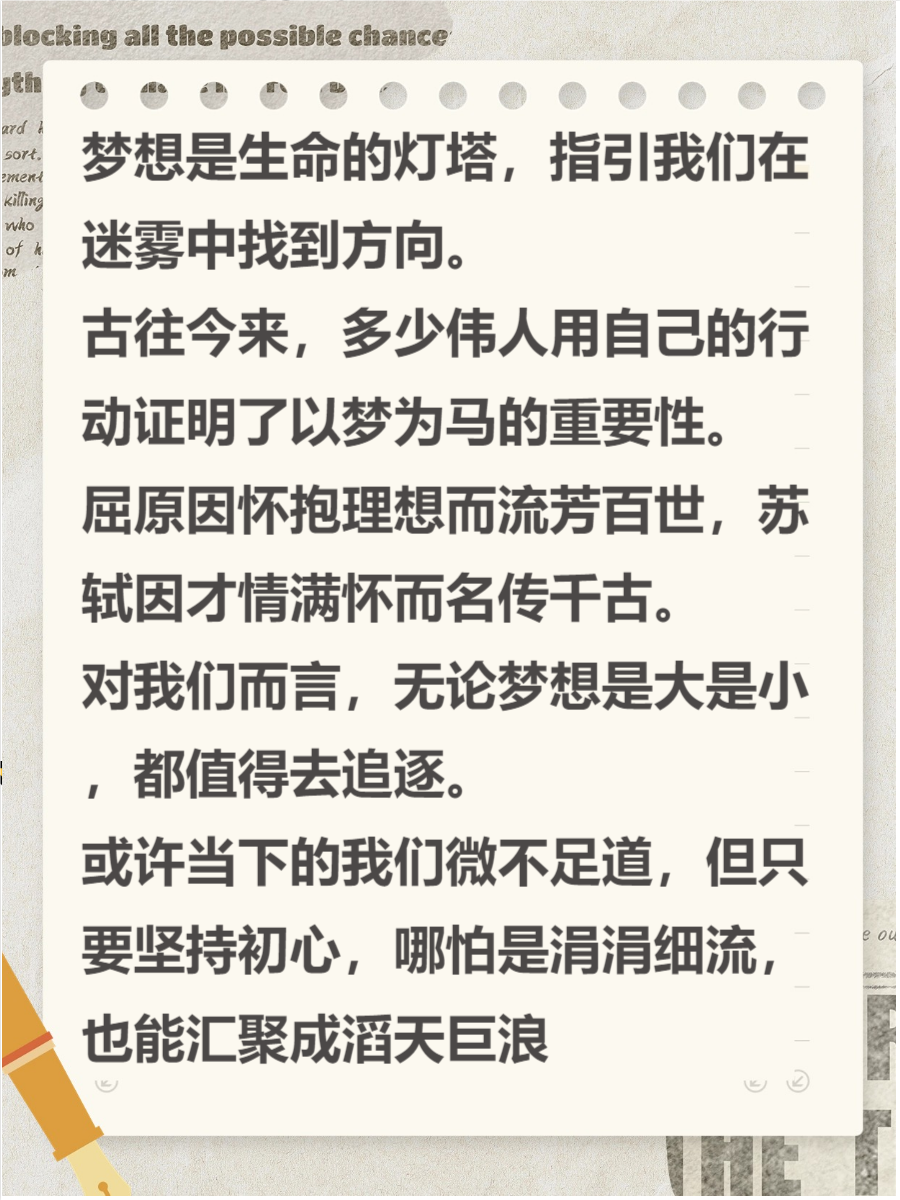
图片来源于网络,如有侵权,请联系删除
(原标题:奔马之上,生命向前――关于力量、美与新年的祈愿)
文/刘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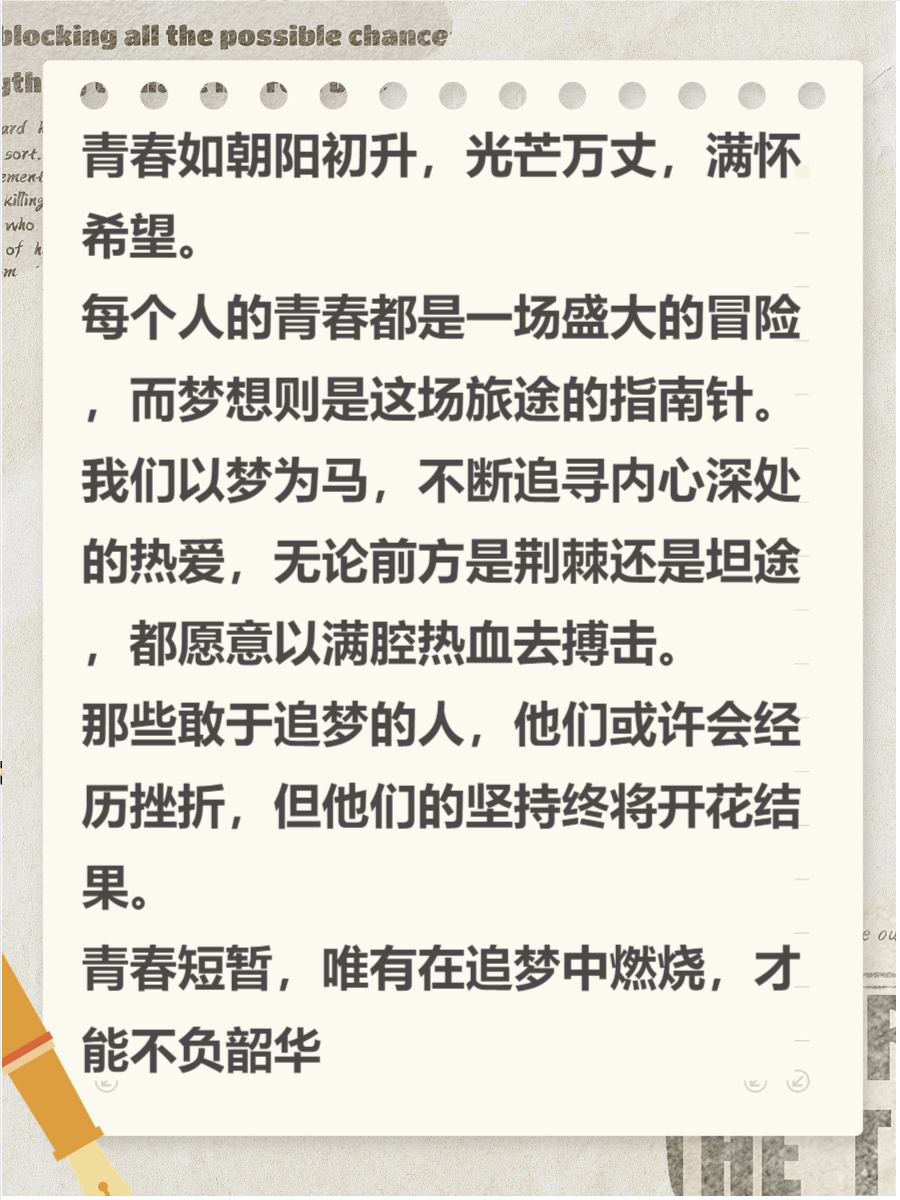
图片来源于网络,如有侵权,请联系删除
又逢甲午,岁次轮转,马年来到。
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里,马从来不只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奇蹄目动物。它早已超越了物种的界限,化身为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图腾。每逢马年,人们总习惯于用“龙马精神”、“一马当先”之类的吉祥话,来期盼新的一年能有一份健旺的精气神。这种期盼,植根于我们这个古老农耕民族对于速度、力量以及远方的永恒渴望。
然而,当我们剥离掉那些被修辞过度美化的金光,重新审视历史长河与现实土壤中的马,会发现它不仅仅是“成功”的图腾,更是人类生存困境的镜像。在漫长的文明史中,马被赋予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孔:一种是被凝视的、被歌颂的“英雄”,它是刚强意志的延伸,是建功立业的符号;另一种则是被牺牲的、被磨损的“生灵”,它是沉默的劳力,是承受苦难的肉身。
回顾它们,不仅是为了应景,更是为了在岁末年初,透过这奔腾的符号,看清生命最本质的坚韧与残酷。我们歌颂奔马,是因为向往其力量;我们抚摸伤马,是因为感同身受于生存的不易。
中华文明的拓展史,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马蹄下的历史。
古人喜马,爱马,颂马,首先是因为马拓展了人的物理边界,支撑了王朝的政治版图。《诗经》三百零五篇,其中就有二十一首诗中含有“马”。那不是田园牧歌式的点缀,而是周代先民在征伐与劳役中的真实喟叹。
名篇如《卷耳》:“陟彼崔嵬,我马虺�P。我姑酌彼金�,维以不永怀。陟彼高冈,我马玄黄。我姑酌彼兕觥,维以不永伤。”诗人通过对马的神态――“虺�P”(疲极而病)、“玄黄”(马变色,喻极度劳累)的细腻刻画,间接表现出征人身心俱疲的状态。在这里,马是人最亲密的战友,也是苦难最直接的承担者。
到了唐代,随着帝国版图的空前扩张,马的形象从《诗经》中的劳苦,转向了昂扬与豪迈。杜甫咏马名句“射人先射马,擒贼先擒王”,道出了马在冷兵器时代战争中的核心战略地位;而“胡马大宛名,锋棱瘦骨成”,则以精准的笔触描绘了那种神清骨峻、不仅属于肉体更属于精神的风采。
这种对马的推崇,凝结在无数汉语成语中――马到成功、千军万马、厉兵秣马、戎马倥偬、金戈铁马、汗马功劳……这些词汇的背后,往往都站着一位英雄,都联系着一场战争,都指向一次征服。在传统的文学叙事中,宝马与英雄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。关云长的千里赤兔,张翼德的乌龙踏雪,赵子龙的照夜玉狮子,马的忠诚与勇猛,成为了英雄人格的一部分。
这种雄性审美的极致,更体现在汉唐的石刻艺术之中。
伫立在西汉霍去病墓前的“马踏匈奴”石雕,整体高1.68米,长1.90米。这尊石刻中的马,骨架匀称,肌肉结实,躯体剽悍肥壮,腿筋劲健,蹄足抓地。它没有嘶鸣奔腾的动态,而是以一种凛然难犯的静态,一只前蹄将一个匈奴士兵踏倒在地。雕塑家以写实与浪漫相结合的手法,使用一人一马对比的形式,构成了一个高下悬殊的抗衡场面。在这里,马不再是自然的生灵,它是大汉帝国雷霆万钧的军事力量的象征,是“犯强汉者,虽远必诛”的立体宣言。
而到了唐代,唐太宗李世民为了纪念征战四方的战马,令工艺家阎立德、画家阎立本刻写了“昭陵六骏”。飒露紫、拳毛�m、白蹄乌、特勒骠、青骓、什伐赤。这六匹马,每一匹都有名字,每一匹都曾身冒箭矢。石刻以高浮雕手法,生动传神地表现出战马在战阵中驰骋疆场的情景。尤其是“飒露紫”,雕刻的是大将丘行恭正在为战马拔出胸前箭矢的瞬间,人马相依,悲壮而深情。这是大唐开国的史诗,是血与火浇筑的丰碑。
时光流转至近现代,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,马的形象再次被赋予了沉重的历史使命。
现代中国画马的集大成者徐悲鸿,一生钟爱画马。他笔下的马,与古人不同,融入了西方的解剖结构和透视学。他作于1941年秋季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的《奔马图》,是其代表作。此时,抗日战争正处于敌我力量相持的艰难阶段,日军企图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彻底打败中国。正在马来西亚槟榔屿举办艺展募捐的徐悲鸿,听闻国难当头,连夜画出此作。
画面上,那匹奔马由远而近,飞奔而来。虽然体格消瘦,但却线条刚劲,笔触带风。画家采用大角度透视的手法,以腾空的一只后腿和交叉在一起的前腿,展现奔马疾驰的速度。弯刀般的腹背,翩然翻飞的马鬃,透露出马内在的精神:沉着而奋勇,坚定而不辍。这匹马,是民族精神的扬厉,是家国情怀的具象,代表着一种刚健有为、自强不息的阳刚之美。
无论是霍去病墓前的石马,还是徐悲鸿笔下的奔马,它们共同构建了一个激昂的“英雄叙事”。 在这里,马是胜利的渴望,是进取的意志。这种审美是如此夺目,以至于我们常常忘记了,在金戈铁马的辉煌背面,还有另一种关于马的叙事――那是属于民间、属于土地、属于女性与牺牲的叙事。
“蚕马”,或曰“马头蚕神”,是中国神话传说中蚕的祖先,这一故事最早见于东晋干宝的《搜神记・女化蚕》。故事讲述在远古年代,有一户贫寒人家,父亲当兵出征,家中只留女儿与一匹公马。女儿思父心切,对马戏言:“若你能将父亲接回家,我便嫁给你。”
家中所养的马听懂了这话,挣脱缰绳而去。不久之后,真的从战场上带回了父亲。然而,当马儿流露出对女儿的依恋时,父亲大为惊异,最终不仅毁弃了女儿的诺言,更强行终结了马儿的生命。
故事的结局诡谲而凄美:马儿的皮毛最终与女儿合而为一,他们化作了又厚又大的蚕茧,挂在枝头。邻人取其饲养,以此树为“桑”。从此,这位化身为蚕的女子,被百姓奉为“蚕神”或“马头娘”。
在这个神话里,马的形象发生了奇异的倒转。它不再是载人冲锋的征服者,而是因情感与信守承诺而献身的守护者。它脱去了英雄的铠甲,化作了吐丝自缚的春蚕,在桑叶间无声地劳作。
在农耕文明的另一面,正是这种如春蚕般的沉默奉献,支撑起了男耕女织的基础。马在这里,脱离了权力的中心,回归到了情感与生存的本原。这种关于牺牲的母题,如同一条草蛇灰线,伏脉千里,最终在现代关于马的影像叙事中,得到了最悲凉也最深刻的回响。
若论当代艺术形式,对马的刻画之深入、表现之丰富,莫过于电影。在光影编织的梦境中,人们试图重建人与马之间那种纯粹的、超越功利的连接。
斯皮尔伯格执导的《战马》(War Horse,2011)便是其中的巅峰之作。这部改编自迈克尔・莫普戈同名小说的电影,本质上是一部披着战争外衣的成人童话。影片别出心裁地以战马“乔伊”为第一视角,串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烽火:从英国乡村的温情驯服,到被迫分离卷入绞肉机般的战场,乔伊流转于英德两军之间,既是战争的亲历者,也是人性的试金石。
斯皮尔伯格用极具古典主义的镜头语言,构建了一种理想化的战争救赎。影片中,乔伊用它纯真无害的天性、不带任何杂质的动机,感动了来自于这场战争对立面的生命。
片中最为人称道、也最具象征意义的一幕,发生在两军对垒的“无人区”。乔伊在惊恐中奔跑,被层层叠叠的铁丝网死死缠住,动弹不得。此时天色渐暗,双方阵地上一片死寂。突然,一名英国士兵举起白旗,跃出战壕,走向乔伊;紧接着,一名德国士兵也走了出来。
在这一刻,枪炮声停止了。两个敌对阵营的年轻人,如同配合默契的外科医生,用铁钳小心翼翼地剪断缠绕在马身上的倒刺。他们甚至在分别时,像朋友一样互道珍重。
这就是电影的魔力。在那一刻,在纯粹的生命尊严面前,战争的政治立场暂时失效,人性的光辉压倒了杀戮的本能。尽管结局是符合大众期待的“大团圆”――男孩艾尔伯特在战地医院吹响口哨,与伤痕累累的乔伊奇迹重逢,实现了“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找到你”的誓言――但这种好莱坞式的温情,更像是一曲关于勇气与成长的精美赞歌。
我们为此感动,因为这是人类良知的乌托邦。我们希望世界是这样的:只要有爱,生命就能穿越火线,获得圆满;只要坚持,所有的分离都能迎来重逢。
然而,这种温情的结局,终究是属于电影工业的。当我们走出影院,面对真实的生存环境时,会发现另一种更为粗粝的叙事。
日本探险家关野吉晴的纪录片《蒙古草原天气晴》(2006),便提供了一部跟马有关的、令人窒息的非虚构文本。这部纪录片没有斯皮尔伯格的光影滤镜,没有恢弘的配乐,只有草原上呼啸的风声和真实的苦难。
片中的主角是一个名叫普洁(Puje)的6岁蒙古女孩。她虽然有着“天之骄女”般的名字,却过早地在马背上承担起游牧生活的重负。她穿着脏脏旧旧的外套和小皮靴,在马背上游刃有余。眼神里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与坚毅。
在这里,马不再是《战马》中那个会被敌我双方共同呵护的“战友”,也不是徐悲鸿笔下那个象征民族精神的“图腾”。在这里,马是财产,是工具,是关乎一家人生计的命根子。
纪录片的走向,残酷地回应了前文“蚕马”神话中隐含的悲剧色彩――马与女性的纠葛,往往伴随着牺牲。
拍摄期间,普洁家里遭遇偷盗,39匹马不见了。这对于一个牧民家庭来说,是毁灭性的打击。为了找回这些马,普洁的妈妈孤身一人深入荒原寻找。虽然最终她回到了家,但在不久后,这位强韧的母亲在去探亲的途中,遭遇了意外,遗憾地永远留在了那片她深爱的草原上。
这不是电影里的剧情,没有最后一分钟的营救。现实的荒原是沉默的,它无声地带走了一位母亲,只留下尚未长大的孩子。
几年后,关野吉晴再次来到草原,但他没能再见到普洁。这个渴望读书、梦想当老师的女孩,在毕业前夕,像一朵过早遭遇霜雪的花朵,凋零在了春天来临之前。
导演的镜头冷静而克制:2004年,当摄制组再次造访,面对的只有照片里普洁那定格的笑颜,和外婆沉默的背影。只有普洁从小骑的那匹枣红小马,已经长成了健硕的成年马,它鼻梁上的一抹白色和茂密的鬃毛,像极了那个曾经驭它飞奔的女孩。
这种“人亡马在”的结局,是对“马到成功”这种美好希冀的深沉注脚。
它让我们看到,生命并不总是伴随着鲜花与掌声。在真实的荒原上,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,没有会为你剪断铁丝网的敌人。只有无常的命运,和不得不继续的生活。
然而,在那匹已经长大的枣红马身上,我们依然看到了一种不可阻挡的延续――即便骑手已经不在,生命依然要在风雪中奔跑。
这或许才是“奔马”最原始、最本质的隐喻:关于生存的坚韧,往往比单纯的赞美更为震撼。 它告诉我们,真正的生命力,不是在温室里被精心呵护,而是在风雪中,即便失去了庇护,依然凭着本能,不停地跑下去。
从《诗经》的吟唱到霍去病的石刻,从徐悲鸿的泼墨到斯皮尔伯格的光影,再到关野吉晴的真实记录,马的形象在人类的精神世界里完成了一次漫长的巡礼。
它既是英雄的坐骑,也是牺牲的祭品;既是理想的寄托,也是现实的镜像。
“亲爱的姑娘,你不要凄凉,不要恐惧!我愿生生世世保护你!”――1925年,诗人冯至根据蚕马传说改编的诗歌《蚕马》,借助马儿之口,对美丽的少女发出誓愿。这誓愿穿越了神话与现实的迷雾,至今读来仍令人动容。
而在现实的草原上,普洁头上的那朵红色绢花,虽然已被风雪掩盖,但并未凋零,它化作了对于美的永恒记忆。
马年将至,我们不需要更多的宏大叙事来粉饰太平,也不需要更多的空洞口号来麻痹神经。在岁末年初的此刻,我们从这些马的故事里,寻找一份直面生活的勇气。
这或许正是我们在马年最深切的祈愿:
愿像普洁一样的孩子,想要读书、想要去远方的梦想,不再被生存的重负碾碎;愿每一个在大时代中颠簸的个体,都能在心底养一匹“奔马”――不为征服谁,只为在踏破冬雪之后,拥有拒绝沉沦、昂首向前的尊严。
马蹄声碎,踏破冬雪,便是春归。
毕竟,在神话与电影的悲欢之外,生活总要继续。愿所有的小马都能长大,愿这奔腾向前的马蹄声,能把大地上的每一个生灵,都带向春风浩荡的新年。
